
跨兒故事 TransStory
簡介
項目內容
跨兒故事項目主要是希望通過客觀的故事敘述,去呈現不一樣的生命故事,在多姿多彩的性別穹蒼下,看見故事中主角們怎樣去創造一個屬於自我的空間,與及面對生活中的困難。
整個項目包括構思、定位、項目策劃、招募顧問/訪談員/受訪對像/編輯/較對/排版美術等人、訪談員培訓、項目資助申請等等。當中進行了比較多的互動,不單止在培訓當中讓學員都提出了自己對項目的意見與想法,故事最終的定稿也讓受訪者參與其中,務求令故事中的細節與方向,都能夠忠於受訪者的意願,能夠呈現出一個有別於以往跨性別故事的新面向。
過往於香港出現過的跨性別故事主要有三類:
一) 跨性別社群主導或參與度比較高的出版 – 為數非常稀少,亦集中於男跨女的內容;
二) 媒體訪問 – 故事的呈現都取決於市場需求與媒體取向,很多時為迎合讀者口味,都會限制了涉獵的範圍;
三) 學生訪問與學術研究 – 因對像並非一般讀者,取材與討論範圍都有所局限。研究所用的故事並不容易給一般讀者消化,也比較少廣泛流傳。
跨兒一詞的起源
這裡我們首次引用「跨兒」這個詞語,跨兒--是跨性別資源中心主席梁詠恩,於2013年在北京工作時構想的一個概念,靈感取自於跨性別理論與酷兒理論的合體。「跨」不單是跨性別的簡稱,而「跨兒」在普通話的語境下,就成了一個獨特的個體理論。當時在中國大陸逗留了接近一個月的時間,由北京同語安排,從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開始,與另一位國內的跨性別者去不同的地方及城市分享跨性別的生命故事。
當時有感「跨性別」這個詞語是從Transgender翻譯過來,初期的社群在接近毫無概念下,完完全全將西方世界的一套照般過來,對華人文化傳統的社會性別觀念,帶來了不少衝擊,也讓不少跨性別者能夠認識及接納自我。但一來不少西方概念不適用於我們的社會狀況,二來在華人傳統裡有不少多元性別的歷史與文化,傳承於我們的民族血脈中,卻因西方理論而未被發展及應用出來,對社群絕少產生影響,也局限了我們發展獨特文化色彩的性別多元理論。
在這樣的一個思維下,於2013年寫下了數百字的框架,但就一直擱在一旁。直到去年聽聞上海有個小組從2015年就命名為「Trans Talk 跨兒說」,後來國內的「跨性別中心」徵詢了「跨兒說」後,正式於2018年2月更名為「跨兒中心」並提倡使用「跨兒」一詞。早前有機會與跨兒說的創辦人及跨兒中心主管討論,原來無巧不成話,我們的想法基本上如出一轍,我也會與Ta們繼續討論及發展出更多屬於華人本土的跨兒論述。
現時,「跨兒」這個詞語已經漸漸地在國內被引用,相對已經廣泛被解讀的跨性別定義來說,「跨兒」將會是一個更廣義、包容性更強的身份,而非一個二元的過渡性標籤。
梁詠恩
關於Ta們的故事
以下部份內容我們會以 「Ta」 這個詞語代替「他」或「她」,Ta的讀音跟「他」或「她」一樣,但不帶有性別之分,讓我們能夠避免不斷重複使用「他」與「她」,也希望提醒大家,在語言文字的運用,能夠尊重各人的性別表達及取態。
編者 序
梁詠恩 Joanne
最近常聽到關於性別認同的反對聲音,其中兩個比較流行的論點是「他們(跨性別人士)連面對真相也不敢,所以要全世界跟著他們撒謊。」和「一旦有了性別承認法,就會被人濫用,連去女廁都會擔心!」
我不想一下子就反駁這些話,說成是完全沒有道理,既然有人說,也得細心思量。到底我們一直在做的跨性別平權運動中,有否遺漏了些什麼?有否在爭取一些人的權益時,不經意地將別人也放在不公平的位置上?我想,平權運動,就是要讓所有人的權益都得到關注,而不是我的比你更加重要。雖然在現實中,我們還是很難讓每一個人都高興,特別面對那些保守的反對聲音。但基於人道立場,我們必須盡力改善受壓者的生存環境及狀況,倡導一個更關愛的社會。
2017年政府開展的性別承認議題公眾諮詢,理論上是要收集社會上不同的意見,集思廣益,好讓政府能夠照顧到不同群體的看法,來制訂一個較為被社會接納的性別承認制度。可惜很多意見的表達都過於情緒化,讓正反兩方都難以聽進不同陣營的憂慮,只是想盡辦法來鞏固自己支持與反對的理由。其實社會上對於一些新的立法建議存有憂慮與恐懼也屬正常,對於同志平權的爭取就更加明顯,我期望社會能夠通過理性溝通,讓政府制訂出能夠釋除大部份人疑慮的法例及措施,才是行仁之道。
有人會覺得講人權太霸道,若我們看到有人受苦,我們會先以自己的利益出發而置諸不理?還是堅持先了解這些人出了什麼問題,才去救民於水火嗎?人道跟人權不一樣,「人道主義(英語:humanitarianism),是重視人類價值 - 特別是關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基本生存狀況--的思想,關注人的幸福,強調人類之間的互助、關愛,與重視人類的價值。」(取自於維基百科)
說跨性別者撒謊,大抵都未曾理解到Ta們所受的困苦。我們還未能很確切地理解到,為什麼有些人出盡辦法,還是沒法接受自己出生時被賦予的性別。我曾打個比方說,若然有一天醫生檢查出來你是雙性人(Intersex),那你會怎樣接受自己原來不是你一直以為的性別呢?有些人窮盡一生,努力改變,嘗試接納社會對Ta們的期望,我們就能夠讓Ta們鬆一口氣,活得像個人嗎?若然擔心女廁的安全問題,就讓我們一起去將安全做好,而不是因為擔心色狼,排斥跨性別人士。
我們希望通過不同的故事,讓社會能夠明白這個群體更多,Ta們的需求與想法都不盡相同,不容易理解。期望真實和多角度的故事,能讓我們看到更立體的世界。香港跨性別群體的呈現,一般較多看到跨性別女性(男跨女),而跨性別男性(女跨男)和性別非二元的呈現較少。這本關於跨兒的生命故事書,開啟了我們紀錄一個更加多元色彩世界的新一頁。
黃結梅 Day
以社區作為保護牆
跨性別資源中心去年曾作過一項研究,發現超過六成跨性別受訪者有自殺念頭,30歲以下的青少年更達七成,嘗試過自殺的人佔四成 。細閱跨性別人士的生命故事時,不禁要問:是甚麼把Ta們推向絕境,痛不欲生?又是甚麼使Ta們極地反彈,發展出抵禦逆境的能力(resilience)?
其中一個故事主角Icarus曾想過自殺,他在學校受盡欺凌,而傷得最深的是家人的排斥和責罵。家人關心的是如何向親友交代子女變性,一句「你要繼續這樣,你跳樓死了我也不會可憐你!」實在刺得太傷了。原來家人給予的只是有條件的愛,是子女按傳統規範行事才能獲得的愛,是给予家人面子才能獲得的愛。另一項調查顯示,跨性別人士面對的暴力最主要來自家庭,受害人中逾六成遭肢體暴力對待 。青少年面對家庭和社會的否定,Ta們如何走出陰霾?
能夠極地反彈,社會支援可謂不能或缺。Yin和Julian都得到同事和上司的支持,鼓起勇氣踏上性別轉換的旅程。工作不只讓他們的經濟獨立,同事給予的支持更為他們戴上保護罩,對抗外力。另外兩位主角Eddie與Icarus更得到女友作為同行者,給予莫大的鼓勵,讓他們決心做自己。Icarus的女友擔起家人的角色,說道:「身邊的人可以陪伴他,讓他知道你在乎他,這就是最有力的支持。」社會支援對於跨性別人士的父母同樣重要,Angela內心交戰期間,有賴良師益友的聆聽,使心中的困擾連同痛症逐漸消失。
書中呈現了五位跨性別男性和一位媽媽的生命故事,每一位主角都是勇者,Ta們勇敢地踏上做自己的征途,建立自主人生。然而,現今香港政策及法例落後,為Ta們途中加設重重關卡。從英國來香港的Eddie,深切感受到本地政策落後了十多年,造成歧視無處不在。六位故事主角異口同聲地反對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要求,除了Eddie認為自我聲明為最佳模式,五位主張只需醫生與專業人士評估及證明,便可改變證件上的性別,減少跨性別人士在工作及生活方面的障礙。廢除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標準,不但是對六十五歲身體欠佳的Ben哥的合理安排,對於不願看見身體器官溶溶爛爛的Yin、希望技術進步後才做手術的Icarus、甚或是憂心忡忡的母親Angela亦是一種解脫。
只有從跨性別人士的角度出發來制定政策,才能適切Ta們的需要,從社區層面增強Ta們的抵禦能力。或許我們都不是政策制定者,但我們可以做到的,也許是在朋友和同事的位置給予支持,又或是碰面時叫聲「Ben哥」──以正確的代號「他」稱呼跨仔,還他們應有的尊重。
張佩琦 Eleanor
我接觸香港的跨性別圈子已有十多年,看着跨性別運動在香港發芽、成長,當中有很多人努力和無私的付出,社會亦隨之而對跨性別議題的看法有所改變:由當初大部份人都不知道什麼是「跨性別」(當年大部份人只知道什麼是「人妖」、「變性」),到今天多了很多人關注跨性別平權、性別承認法等等(除了報章、傳媒上多了聲音,在社區也看到市民對跨性別議題的支持,例如去年有一些街坊會過來跨性別資源中心說聲加油)。
但是爭取平權的路仍然很漫長,不少公眾人士仍然對跨性別不認識、不了解,這些誤解、無知亦構成反對平權的聲音,甚至對跨性別的恐懼。今次出版的書除了進一步增加讀者對跨性別朋友的了解,亦是香港出版有關跨性別刊物的另一突破。因為一直以來大部份的刊物都聚焦在跨女身上,很少機會聽到跨仔的心路歷程。這本書不但讓我們聽得到跨性別群體多元的聲音,亦讓我們聽到不同跨仔的生命故事。與一般的訪談不同的地方是今次的撰文讓受訪者有自主權,因為受訪者會閱讀其初稿,在有需要的時候作出修改,讓受訪者的故事如實地與大家分享。
作者感言
Natalie Yim - Icarus 故事
這次是我第一次接觸跨性別人士,開始時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了解後才發現他們也許不是社會一般的主流,卻並不怪異。他們和我們一樣,只是出世紙上的性別不是他們所認定,所以透過不同的方法令一切回到正軌。當他們如此努力去做自己,去做好自己,我們應該尊重。
Minnie Chiu - Yin 故事
第一次接觸跨性別人士時,我感到很緊張。相處後,我才知道他們和我們沒有分別,有不同喜好,不同性格。雖然我不認識變性前的他們,但每當談及他們變性的感受,我在他們的眼睛看到光亮和希望。我想,這就是所謂做自己的喜悅吧 ;)
Carmen Wong - Julian 故事
其實這已是我第二次訪問跨性別人士,大家經歷過或經歷中的過程也非常接近,而這兩次的訪問內容也不同,令我了解到他們自身遇到的困難外,更令我明白到他們正在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他們亦是一群擁有強大心靈的戰士,不但想幫助圈內人,亦希望令下一代的年輕人建構更和諧的社會。
Eunice Chau - Angela 故事
「跨性別人士」這個標籤,我上課聽過很多遍,但面對面接觸還是第一次。透過聆聽跨仔的故事,更確實知道他們面對工作、家人等的難關。一些平常人看似簡單的日常處境,他們需要更多的勇氣,去忠於自己的身份。隨後,更有幸與跨仔媽媽面談。從另一方向看跨仔家庭的處境,更了解到接受自己骨肉的換性身份並不容易。這群每天努力做自己的人,不是要社會「好心認同」,而是透過了解,知道他們與我們一樣努力生活。不再細分你或我,不就可以了嗎?
Lanlan Yu - Eddie、Ben哥故事
原來,我對跨性別人士的生存狀態所知甚少,彷彿Ta們從來不在身邊「現身」,而原來那種欲現身的願望、欲被認同的願望如此強烈,卻又隨著恐懼現身、疑惑現身而「消解」在大眾視野。Ta們面對內在自我,外在主流社會雙重乾煎之下,「現身」是充滿矛盾與痛苦。感激Ta們在這本書坦誠地說出自己的故事,但願在面對自我的議題,世界少點惡意與無知的磨難,但願Ta們溫柔地擁抱自己,我們也溫柔地擁抱起彼此。
跨兒故事
心疼孩子走過探索性別的艱難旅程 - Angela
文/Eunice Ch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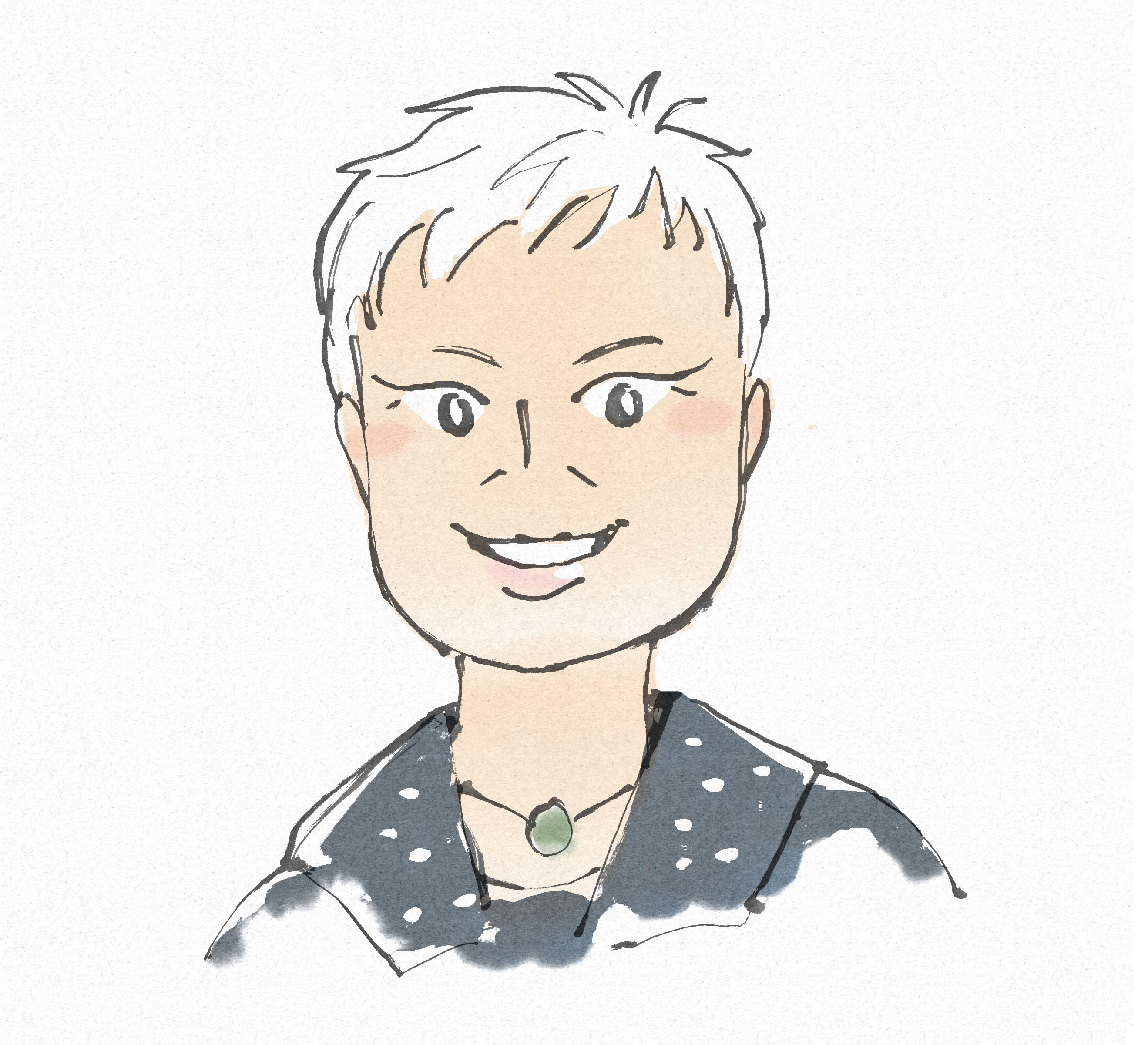
回想2016年的2月,27歲的「細女」向家人坦承自己跨性別的身份,當時理性的Angela,沒有像肥皂劇中的母親質疑或怪責自己的孩子,反之,只有對自己孩子無限的信任。回想起孩子出櫃時寫給家人的信,裡面附有跨性別資源中心「拆解性別認同障礙」小冊子,「細女」更與Angela說:「我上網查過,問卷也做過了,最後肯定自己跨性別的身份。」
Angela明白到,探索性別身份的旅程絕不容易,除了心痛孩子需要一個人走過這艱難的旅程,更多的是欣賞孩子的堅強。
「由『我一對女兒』變成『我一對仔女』」
「我知道細女的變性決定之後,都有心痛,因為知道整個過程很不容易。而他可以一個人行,好犀利,亦很有勇氣,同時省卻我很多煩惱。如果我早知道,我會不知如何與他探索。」Angela從前於商界工作,提早退休後,近十多年則從事輔導工作。閒時會參加不同的工作坊,一直主張打破社會的性別常規,追隨自己想過的人生。她常說,小朋友只要知道後果,為自己負責任,做甚麼都可以。可是,這樣的一位母親,卻為自己孩子變性的決定,走過了一段難以忘懷的心路歷程。
表面理性的Angela內心曾交戰連連,知道孩子的跨性別意向後,內心複雜和混亂,無法平靜地集中精神於限期前完成當時修讀臨床督導的論文。更甚的是,連身體都開始響起警號,左手手腕像捉緊着甚麼似的,痛症久久未能治癒。Angela說:「以為接受就可以,原來只是理智上,但心裡面還是有暗湧,令身邊每件事都十分混亂。」
再堅強的Angela,亦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所有事實。那時,她選擇了一位良師益友作聆聽者,從中得到心靈上的支持。「她很明白我,可以走進我的內心,讓我可以講,可以釋放。我與她互相信任,毫無保留將心底話說出來。」由那刻開始,Angela慢慢放鬆緊握良久的左手,痛症亦漸漸地與混亂的狀況一同消退。
Angela坦言,孩子的改變其實不多。外貌上,看着「細女」慢慢由女兒身,轉變成一身肌肉的陽剛男兒,稱謂就由「我一對女兒」變成「我一對仔女」,亦改用他的新名Billy(化名),孩子還是她二十多年來愛的那一個「細女」。
「讓跨性別人士在社會中被看見,讓孩子被看見」
Angela除了面對孩子性別認同的掙扎,更要向親戚坦白。Angela不只是一個人面對,也有大女和丈夫一路陪同,大家有商有量,互相溝通。在出發前往家庭聚會之前,會商量與哪幾位親戚坦白,又約定當有人問及時怎樣作答。有趣的是,雖然作了萬全的準備,沒想過根本沒有親友主動提問。Angela回想,一方面,在家族聚會中,Billy一直作中性打扮,更是一名運動健將,身型健碩,沒有人注意到他已經接受荷爾蒙注射。另一方面,香港仍視性和性別等議題為禁忌,沒人會突然主動提起。Angela稱:「他們不敢問,亦不懂問,即使問了,亦不懂之後如何對答。香港仍是一個十分保守的地方。」
即使面對如此保守的香港,Angela與孩子仍盡力帶來改變。沒有人問,Angela和Billy則主動與幾位信賴的親朋戚友坦白,尤其Angela亦不想隱瞞身邊幾位知心好友。貼心的母親與朋友碰面前,都會問准Billy,希望可以公開他的性別身份。Angela坦言,這過程不是要求他人認同Billy的身份,只是毫不保留地向好友說出心底話,讓跨性別人士在社會中被看見。她現時已獲得不少好友的支持,可見出櫃不再是孩子一個人的掙扎,而是與家人一起攜手,走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寄望未來有一天,春天真正來臨」
可惜,社會對跨性別人士的認知仍然不足。雖然Billy已將身份證上的名字換成男性化的名字,但性別一欄仍未能按個人意願更改,令他不敢在公司出櫃。而且他的身體因荷爾蒙影響而漸漸變得男子氣,造成生活上種種不便。例如為了確認他的性別,公司職員專用健身室不同的職員都曾向他仔細查問。Billy為免為難,寧願預先穿好所有運動裝束,也不會進入男或女更衣室。這些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作為母親的Angela也感受到孩子在生活上的不易。
Angela回想Billy為了轉換性別,兩年來在威爾斯醫院接受診斷及荷爾蒙注射,又到美國做上身手術。不同的專科醫生也發出證明信讓他以另一性別生活。可惜,兩年後的今天,Billy仍因為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而不能轉換身份證上的性別。在出入境時更不時發生令人尷尬的場面。有見及此,Billy到美國接受醫生檢查及手術時,特地找來母親和姊姊同行,除了家人是一枝強心針,更重要是在職員留難時,有家人幫忙解釋。Angela說:「換了性別,他直行直過便可以,不用遇到種種問題和關卡。」作為母親,她只想孩子活得開心。雖然Billy日後會接受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但若香港通過性別承認法,得到醫生證明信那刻已可早一步轉換性別,屆時在日常生活上面的關卡及質疑便可大大減少。


Angela望着畫作,那是以前與孩子一起學畫畫時出版的畫冊。與孩子的性別探索歷程已過了兩年多,Angela難免感到孤寂。幸而她在這孤寂的境況中仍保持希望,正如畫中的樹木雖然變得光禿禿,但樹枝仍然堅壯及富生命力,待春天來時就會再次發芽、成長。現在Angela只寄望未來有一天,春天真正來臨,Billy就如另一幅花團錦簇的畫作一樣,有另一個燦爛的人生。
PS
「現在走的路十分孤單,只有寥寥幾個人。雖然遠望有幾個人,環境亦不錯,但仍會覺得寂寞。」

六十五年的人生,我只開心十五分鐘 - Ben哥
文/Lanlan Yu

Ben哥說他65年的人生只開心過15分鐘,人生要有多艱難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你聽著他的故事,一誕生來到人世,立即被生母拋棄,假若養母沒執他回家,就肯定會凍死在那個春天──他出生在象徵循環裡新生的季節,卻險些死去。他活了下來,此後的人生仍然是一次又一次險些死去,像一場又一場的試煉。悲傷事件他牢牢記著,會連珠炮發地訴說,身體的苦難,精神的苦難或者愛情的苦難,還有那個性別的苦難。他一出生便不是以他應有的性別誕生,一直不知曉藏在心裡的鬱結終結成石頭,他在「她」的外殼裡揪著心地過活,65年人生的調子灰暗。
他在很後來才擁有打從心裡的快樂──那個快樂的15分鐘,一次在社區會堂的粵曲演出,他負責鑼鼓演奏,司儀向觀眾介紹Ben哥「靚仔師傅」,他笑到合不攏嘴,落力又光芒四射地完成整場演出。「65年的人生,我只開心了15分鐘。」他說,不過是一句還給他應得的肯定和認同的稱謂。
「養母當我公主養,但我想做王子」
幸好他的人生還有疼惜他的養母,出世只得五磅幾,養母也不知道這孩子養不養得大,一個寡婦,丈夫在香港淪陷時被日本仔弄死了,就和Ben哥相依為命,盡心盡意地養育這個孩子。「她花好多心機,物質上供應得好足,捱得好辛苦。現在再難找到人這麼疼我錫我。」Ben哥想一想,再說:「她當我公主養,但我想做王子,所以我不開心。」
小學時養母要他學芭蕾舞,著粉紅色蕾絲舞裙,要他穿上裙子打扮得像小公主。「她錫我,但給我的或者要我學的完全不適合我。」但Ben哥從不敢反抗養母,默默地順應她的意願:「她當時是護士長,打理四間胸肺科,四百個手下,個個都不敢向她說不,我更加不敢出聲。」中學讀女校時,其他TB(較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也一樣短頭髮著校裙,他為躲避衣櫃裡的其他裙子,只好一天到晚穿著那套校服裙,到夜晚八點他仍穿著,用各種方法在養母前演戲,把心裡的王子願望隱藏下來。
Ben哥從懂性開始就意識自己是男的,一旦有人叫他阿姐,他非常生氣,「阿姐阿姐」是很具傷害力的稱呼,他一輩子都在和這個刺耳的稱呼角力。「現在我家樓下那個死人看更,成日叫我阿姐靚姐,我好嬲但又不敢罵她。其他人也猛叫你阿姐阿姐,好火滾,我唯有當那些人痴線,沒有見識,安慰自己,但仍然非常不開心。」
25歲那年養母第二次中風救不回來,彼此互相照顧對方十幾年,最疼自己的人走了,自此就剩自己一人。那種焦慮、無助、性別的壓力,慢慢累積在身心裡,三十多歲時Ben哥的身體已經很差,常常覺得自己就快死。
「那時的情況比現在差,手可以完全沒有知覺,身體一邊冷一邊熱,好辛苦,以為自己會死。」命運時常給他難題又會給他貴人,直至遇上一位中醫師,跟著他治療了三十多年,身體慢慢復原,死不去。吃了二十五年中藥調理打好身體的底子,也會因為吃了不該吃的寒涼食物或精神緊張、壓力等令他身體虛弱。「最慘是無助,沒有人幫忙,一個人決定一切事情,真的好無助。」Ben哥說特別現在他老了,孤獨的感覺更強烈,連自己一人上街也心驚。「行又行不到,沒有力氣,因為沒有人陪,最遠只能去新蒲崗,連黃大仙也不敢去。」
「希望像楊過找到我的小龍女」
Ben哥談到他的戀愛史,說一直憧憬自己像楊過找到他的小龍女,但一直找不到,1983年以來他都是自己一人。中三那年他第一次想追求心儀的女同學,長得漂亮又像對他有意思,就向他學柔道的導師Eva說起,她就說要幫他追求。「我心想,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我為什麼要你幫我追。不久我和那個喜歡的女仔在一起,經常去她家找她,後來發現她一腳踏兩船,原來Eva一路偷偷瞞著我找她。」
「被信任的人出賣真的好受傷害。」Eva是當時Ben哥信任的朋友,甚至稱兄道弟。
第二段的感情是另一場噩夢。1972年Ben哥入政府工作,被迫每天著裙,當時有個新人跟著他工作。「她以為我是男人,即使我著裙,她仍好有興趣想和我在一起,我不是很喜歡她,但接受了她。上床時她意識到我不是男人,就想飛我,開始對我冷淡。」Ben哥和這個女生拉拉扯扯了十年,甚至令他患上精神病。「當時寫字樓有另一個女仔追我,被她發現,大鑊啦!她在家扯我頭髮不給我睡,又上寫字樓等我,更寫了信去署長話我搞同性戀,我長時間沒法睡覺又被疲勞轟炸,結果患上了輕微的精神分裂。」
這兩段關係令他對人再沒有信心,連續說了兩次──對人完全沒有信心了。「83年以後就再也沒有遇到一個真正喜歡我的人,是否我人太好,其他人都會利用我?那個新追我的女仔見我病就放棄我,和其他男人一齊。我給女人累死,我怕了她們。」
「我從穿裙的文員、輔警到靚仔鑼鼓師傅」
Ben哥從72年至93年打政府工,當年規定男的要著西裝打領帶,女就要穿裙子上班。「好辛苦,我從第一天上班就好想辭職,那時養母知道自己快挨不住,仍叮囑我不要辭職,在政府做到退休。結果我做了二十年。」當時Ben哥短髮,舉止粗魯,卻被套在裙子裡,在寫字樓或者去女廁受盡別人異樣目光,被人當作男扮女裝,恐同恐跨情緒無處不在,那時他並不知道自己屬於跨性別人士,以為自己是TB而已。
「我以前以為要做完手術才是(跨性別),但我沒有做手術,直至六年前認識跨性別資源中心主席Joanne,除了養母,她是另一個關心我的人,後來才知道自己是跨男。」「跨男」的性別認同對Ben哥而言特別重要,他終於了解自己為什麼抗拒著裙,討厭別人叫他「阿姐阿姐」,突然豁然開朗了。「以前兼職做輔警做得特別開心,我頂頭上司認為我是男的,其他警察也當我是男,叫我Ben哥,而且巡邏時可以著便服,恤衫牛仔褲,所以那段日子比較開心。」
2011年Ben哥參加了基恩之家,找到了認同他的社群,但因為當時跨性別圈子太少,他不太感受到別人的了解和關心,後來參加跨性別圈子的聚會,因他們屬於年輕一群,最愛聊做手術。「你知我條人命怎樣做手術?有時不太投緣。」Ben哥不想自己一個,他想認識更多不同的朋友,互相支持,他也想別人關心他、在乎他。
「那你沒有想過做手術?」
「我三十多歲時身體已經不好,患過精神分裂,生活太多憂慮積壓在心裡,兩次幾乎覺得活不下去,也沒有那麼多錢做手術,要賺錢養活自己,就沒有再想了。」今年Ben哥已經65歲,也無法承擔手術的風險,身份證性別依舊是「女」,晚年生活依舊承受「女性」標籤加諸他身上的痛苦。香港主流社會在討論性別承認法,都認為必須通過性別重置手術才可以認同其性別,這個主張會否剝奪了一班身體較弱的年老跨性別人士的權利?
Ben哥說:「65年的人生,我只開心了15分鐘。」「靚仔師傅」不過簡單的一句對其性別的肯定和認同,如果你心疼說這句話的人,會希望他往後有更多開心的時刻,而不該只有那15分鐘。
性別承認法 香港比英國落後十幾年 - Eddie
文/Lanlan 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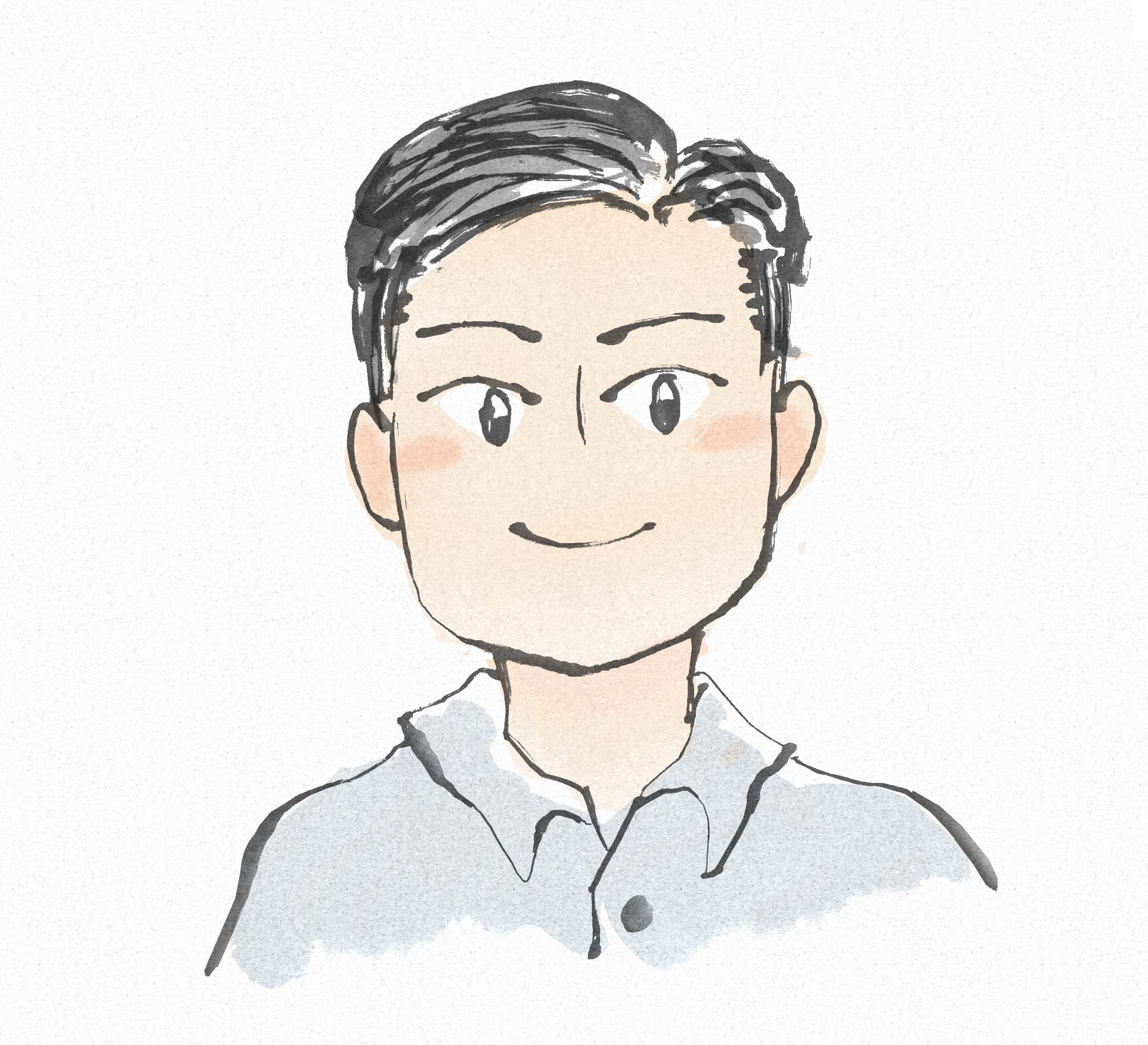
逸東,是Eddie上年為自己改的新名字,因他喜歡兔子,喜歡東方,他還笑說:「加上發音挺好聽。」日出東方,萬物甦醒,而日光將萬物的裡裡外外照得明媚。Eddie坦然的笑顏和溫柔,與名字相襯,一個沒有陰霾或灰暗的跨仔,總是笑,總是不憂不愁。
「我中文不好,從沒有想過能為自己改中文名,這一兩年變化好大,連名也改了,代表我想轉變,想自主。」儘管父母有時改不了口,忘記他是女兒還是兒子,也忘記他新造的名字,但也不再足以掛齒。
去年三月,Eddie為自己做了人生中至為重要的決定--改掉香港身份證上的名字,開始注射男性荷爾蒙,還預備在今年十二月到台灣進行上身的性別重置手術,切除乳房。他期待著來年的夏天赤膊出海,游泳、曬太陽。
他一臉雀躍,笑著說:「(手術)安全緊要,靚都好緊要,要畀人睇架嘛。」
而這個重大的人生決定,足足推遲了二十年,直至兩年前他認識現任女朋友為止,成為他三十多歲給自己的一份禮物,也是他與現任女朋友共同進退,互相扶持的第一件事。
「睡前默默祈禱 醒來變回屬於自己的身體」
故事總是由最早的性別記憶開始。「早些日子妹妹重提起一件事,五歲那年我穿著爸爸的睡衣,而她穿上媽媽的高踭鞋,我們拍了一張好搞笑的合照。」合照像一種很早的證明,但Eddie的記憶發生得更早,三歲的他知道世界上有分男、女,但每當別人問他是男是女,他定必回答:「我是男仔。」但肉身是天生,無法如願,他總在睡前默默祈禱,希冀這只是一場夢,第二天醒來就能變回屬於自己的身體。
Eddie幾歲開始在英國生活,直至十年前因為工作,搬回香港。英國這地方待年少的他很好,沒有為他留下成長或掙扎欲絕的陰影,也沒有任何異樣的目光或企圖扭轉他,即使身體依然是他所不喜歡的。
「一直以來我都以男仔的方式生活,身邊從來沒有任何人會提醒我是女生,而大家都喜歡這樣的我,對我很好。」包括父母對他從來持性別中立的態度。Eddie走路大剌剌,喜歡玩槍或踢波也好,父母從不加以壓抑或責難。直至上年他回英國見了兩次臨床心理學家,決定注射男性荷爾蒙踏出第一步時,才第一次把自己的性別疑雲娓娓道來,仔細回憶一些幽微的疑惑與心事。
「小學我讀女校,最怕穿裙子,我差不多參加所有校隊,一星期五天練習,我盡量著運動裝、運動褲返學。中學讀寄宿學校時,同學叫我『余先生』,我和一班鬼妹同宿,她們驚訝地說,你不只外表像男生,連聲音也像男生。大學我主修電子工程,班上九成男生,我覺得非常舒服,覺得更屬於這個群體,說什麼做什麼也不用介意,好自由。」Eddie繼續說:「等於我去男廁,我也有這種感覺,假如你叫我去女厠,我反而覺得好奇怪,渾身不舒服。」
「一個人變成兩個人的事」
為什麼二十年後才出現人生的「跨」越?
Eddie怕血、怕痛,從不敢想象面對性別重置的手術。「大學時我在網上認識一個跨仔,他做了全身手術,告訴我過程,首先他說要一輩子打荷爾蒙針,打針已經恐怖,他又傳來下身手術的照片,更恐怖,我停止再想,之後再算。那時我才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原來是跨性別,英國待2004年才設立性別承認法,當年未立法,所以沒有想太多。」也因為生活環境和人待他好,即使性別認同比其他人迂迴,從沒有人把它定義為問題。
真正的自覺與改變的契機,來自兩年前Eddie向女朋友的一次「出櫃」,因為女朋友的疑惑,他才真正思考自己的狀況,著手處理一直延遲、關於自我的事。
「一開始她並不知道什麼是跨性別,她以為我是女同性戀者,就當我女朋友,不停叫我『女朋友』,又用『她』稱呼我,我覺得怪怪,認識她一星期後,我們結伴去峇里島旅行,我在氣氛輕鬆的環境下對她說,其實我想你叫我做『男朋友』,我不喜歡你叫我『女朋友』。後來我知道她搜集資料,和朋友討論我的情況。」
Eddie後來見到ViuTV《啪啪聲》吳穎英醫生講跨性別,立即叫女友看,說:「你看,我是這樣子。」這樣就開始他們的討論,女朋友的支持下,他真正思考,原來真的有問題,女朋友幫忙找吳醫生傾談了解狀況,開始他人生重大的改變。
上年Eddie加入跨性別資源中心幫手 ,點子多多的女朋友出謀獻計,參與討論。之前她不是太了解跨性別是什麼,所以也做了很多資料搜集,一個人的事變成了兩個人的事。「我女朋友錯認我是女同性戀,但事實上我是跨性別。她說過,做回你自己就好了,她屬於靈性的人,我知道她明白我。」
「香港比英國落後十多年」
Eddie說,自小的遭遇到底幸運,在英國成長,從來沒有人歧視他,也沒有留下陰影。回來香港生活十年,顛倒的是另一種形態。Eddie在香港較開明的英國公司工作,但公司以外的日常生活卻充斥著無孔不入的歧視和無知。「我無法使用電話銀行服務,想取消張卡也不行,必須親身上門,就是因為聲音,資料顯示我是『余小姐』,對方一聽就問,你是誰?我答,我就是,對方就叫我落分行辦理。在英國完全沒有問題,因為一個女人也可以有一把男人聲。」
還有他認識自小在香港成長和生活的跨性別朋友,聽來的故事都灰暗憂鬱。
「有人不喜歡自己是跨性別,不願承認。我想叫一位在威爾斯醫院剛完成全身手術的跨仔分享,他八月才剛做完手術,屬於少數連下體也重置的跨仔。他對我說,不想承認自己是跨仔,表明他是男人。我好衰,就說,即使你做了手術,也不是Cigender(順性別,性別認同與出生時被指派的性別一致),你就是跨性別。他說,你不要理我,我寧可做個Fake man(假的男人)。他經常不開心,灰暗,沒有女朋友,他不敢告訴別人自己是跨性別,說香港實在太多歧視。」
「性別承認法很重要。現在香港沒有法律規定,即使你做完手術,更改了身份證上的性別,但不代表法律上承認我是男性,這非常重要。沒有法律約束,不能保障私隱,無法不讓別人知道我以前的性別,例如電訊公司仍可以找到以前的資料,叫你『小姐』。幫你的身份證改掉性別,只不過是行政手法,沒多大意思。」現在英國性別承認法的討論已經進展到自行決定法定性別,「香港比英國落後十幾年。」2018年的香港討論應否跟從英國模式,即2004年英國性別承認法。第一次見Eddie,他已經這樣說了,在英國成長的他,觀點也比其他人走得前衛,最理想是自行決定就能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這也是不少歐美國家走的方向,實踐上來也沒有影響到其他人。
「有人說,讓醫生之類的專業團隊把關,但我不覺得醫生有如此大權,醫生也是人,會下錯決定,我不想他們錯過任何一個人,隨時可以限制及主宰一個人一生的決定。我們是人類,有不同需要,我們要性別承認法,過更好的生活。跨性別人士也努力工作,讀書,我們也是有能力的人,不是榨取社會資源,我們同樣在創造資源,投資和貢獻社會。」此時,溫柔的Eddie也說得堅定。
請重新給我一個性別 - Icarus
文/Natalie Yim

別人的童年都是儲錢買玩具,只有他在小學五年班聽聞「變性」一詞後,已經希望儲錢去變性。「變回一個男生」就成了Icarus最大的心願,18歲生日他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 ── 選擇做自己本來的性別。Icarus說:「長大後清楚甚麼是變性,我就下定決心,在18歲生日當天看醫生。」他坦言實在討厭自己的胸、「雞仔聲」和所有女性性徵。只要能變回男生,他甚至不介意做手術,不介意後遺症。在我們眼中,這是很勇敢的決定。
「我想過工作幾年然後就自殺」
Icarus言談間總愛開玩笑,是平易近人的陽光男孩。提及可以做男生,眼中總閃爍著光芒,但原來在18歲前,他曾想過結束生命。「從小到大因爲我行為表現像男生而受盡歧視和責備,心理壓力很大,加上自信心低落,所以想過讀完書出來社會工作幾年,享受幾年,然後就自殺。」因為Icarus比較男性化,在中、小學都逃不過被欺凌的命運。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班主任只留下一句:「你知道自己問題出在那裡,同學都不喜歡你,分組時都不想與你一組。」一個不諳世事的中學生就這樣給老師和同學聯合排斥,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自己男性化的形象。老師未曾了解過Icarus的性別認同,不曾問一句發生了甚麼事,就認定是Icarus的性格有問題。
除了學校,家庭也無法了解Icarus,家人由此至終都反對Icarus變性和接受荷爾蒙治療,嘗試用各種理由阻止。Icarus指家庭是最大的壓力來源,也是跨性別人士最大的困難。「我很怕媽媽,從小到大,她一下命令我就會聽話。當時我表現得像男生,媽媽就不斷買女性化的衣服給我穿。我接受荷爾蒙治療後,媽媽突然哭了,說些難聽的話:『 你叫我如何與人交代啊!你要繼續這樣,你跳樓死了我也不會可憐你!』」 作為Icarus最重要的生活圈,中、小學階段所承受的歧視和家人給予的壓力令Icarus喘不過氣來,甚至一度找不到人生意義而有自殺的念頭。幸好,上帝雖然關了一扇門,卻開了一扇窗,讓他看到窗外一片更絢麗的風景。升上副學士後,Icarus結識到接受他的朋友和女朋友,開始有社交生活的他終於發現世界原來並非只有黑暗一面。
「在我自卑時,是她協助我建立個人信心」
踏出第一步往往是最困難,在滿懷期待的同時也會恐懼和遲疑。Icarus能踏出這一步,全賴女朋友的支持與陪伴。Icarus說:「在我猶疑時,女朋友鼓勵我相信自己作為成年人的決定,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在我自卑時,是她協助我建立個人信心。」他望著正在陪伴做訪談的女朋友Samantha,眼神充滿喜悅和感動,令人感受到滿滿的愛。
Icarus憶述當時去到醫院門口反而猶疑不決,入去還是不入?如何開口?入去該說甚麼?即使在心中構想了千百次,還是不知如何面對,幸好當時Samantha陪在身旁給予支持。他倆好像心有靈犀,認識不久Samantha已經感到Icarus想做男生這壓抑於心底的秘密。她比Icarus更心急,想Icarus可以盡快做回自己,Icarus興奮地說:「當時是她一直催促我見醫生、接受荷爾蒙治療,想我快些變回男生。現在大家都會覺得我是男生,真是開心很多!她知道我希望可以做回自己, 看見我自信心多了,更認同自己,我知道她比我更興奮。」
支持不僅僅是言語上,更是行為上。從做資料搜集到陪Icarus看醫生,Samantha在Icarus最大壓力與不安的時候給與支持和包容,這些事情連家人都未必做得到。Samantha不但是陪伴者,更是生命同行者,Samantha說:「我覺得踏出第一步往往最困難,因為你需要很大的勇氣。我當時陪他去,是因為我建議他去的,其實對所有跨性別人士而言都是一樣,若果身邊的親人陪伴他看醫生,讓他知道你在意他,這是最強而有力的支持。」Samantha坦言Icarus在接受荷爾蒙治療後脾氣大了,很小事都會吵架,但她認為這都只是小事,最重要是人開心,信心大了可以勇於做自己。Samantha認為真正的支持是理解與陪伴,將心比心,唯有這樣才能令對方感受到被明白,這條路便不會那麼孤單。
「我們下定決心做自己,希望得到社會支持」
在很多人眼中,選擇成為跨性別人士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可能是年少無知,可能是一時衝動。而這個決定令朋友擔心,令家人傷心,看似十分不負責任。但事實上,只有當事人才明白,為了這個決定他們要付出多大代價。做自己,對大眾而言尚且不易,何況是對性別小眾。Icarus是幸運的,他遇上了無條件支持他的人,讓他最終勇於追求,認同自己。以他的男性樣貌,在人生路上重新出發。
隨著社會對跨性別的關注,性別承認法已經提上議程,但現實是因為公眾教育不足,香港市民對跨性別人士仍有很多誤解。但Icarus依然感恩有性別認同診所,給予他希望。在香港做手術很困難,案例不足加上技術未成熟,風險很高,而且手術不是想做就做,Icarus當然希望越早越好,但要等醫院審批、排期,做完一個階段的手術又要等,再檢查、排期,一排便排上好幾年。
現時性別承認法諮詢的其中一個建議,是不需要手術和荷爾蒙治療,兩年後通過醫生評估便可以修改身份證上的性別,Icarus和Samantha都深表認同。Icarus說:「如果有性別承認法,我可以等香港的技術比較進步才安排時間,至少等醫院設備比較先進時再完成重置手術。」為了改換性別而犧牲健康的身體是不合理,重置手術風險很大,即使荷爾蒙治療,其副作用也不是人人承受得了。跨性別人士在心理上接受自己已經夠困難,或許我們並不理解,但在他們追求做自己的路上,不去強加這些苛刻的條件,已是最大的支持。
為自己戴上防護罩 逃離囚困已久的身體 - Julian
文/Carmen Wong

Julian,有著混血兒面孔卻是在新加坡出生的香港人。他在一個很傳統的家庭長大,由於爸爸要到處公幹的關係,他從小便要經常跟著爸爸遷徙。同樣因為爸爸要經常外出工作,Julian跟家人的關係比較疏離,他說:「我能理解爸爸工作的辛苦,明白他身不由己。 」
在Julian的眼中,爸爸是個大男人,他從小就不敢反抗爸爸的命令,壓抑著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做個爸媽眼中的乖寶寶。為了避免媽媽的責罰,媽媽買裙子給他時,他從不反抗。他害怕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不哭、不大聲只懂得微笑才能夠得到父母的稱讚。
「想過怎樣的生活 應該由自己選擇」
小時候Julian與弟弟一起洗澡後,就透過畫畫表達自己的訴求,用畫筆素描弟弟的下體遞給爸爸看,想告訴他自己也想變得跟弟弟一樣,結果卻被爸爸痛罵,從此以後在這個家裡不准談及任何有關性別的話題。
Julian在13、14歲時,一時衝動剪了短髮,當時他心驚膽顫,怕再次面對家人重重的責罰。每次嘗試為自己作出改變,換來的卻是與家人日益轉差的關係,令他驚覺任何非女性化的打扮就會觸怒家人,亦覺得家人從來不懂得關心他的情況和感受,只著重他的外表和裝扮。所以關於他最近的改變,Julian決定先斬後奏。用荷爾蒙藥將近兩個月,爸爸發現他的聲音有明顯的轉變,從外地打電話痛罵他一頓:「是我養育你,你為身體作出改變是對我大不敬。」Julian不同意這句話,認為自己的人生應由自己作主,不存在誰欠了誰。雖然如此,他強調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將來亦會好好照顧他們,但對於自己的身體,他覺得應該由自己選擇。
父母一直強硬的態度導致Julian無法與家人坦誠相對,更間接令他經常否定自己的性別認同,不斷為自己尋找藉口:「做Trans好麻煩,要顧慮別人的眼光,又可能要做手術,我一定不是Trans。」但再多的藉口也無法掩蓋內心深處的渴求,他一直猶豫不決,心底裡還是想脫離自己的身體。小時候,無力反抗的他只能隱藏真實的自己,但現在他已經找到一份自己擅長的工作,終於可以決定自己人生的道路。
Julian憶述:「可能因從事創作工作的關係,身邊的同事都很隨和,就算上司知道變性此事都表示支持,所以我蠻喜歡整間公司的工作氣氛和文化,亦知道大家對我的接納不是必然,我一定好好珍惜。」上司對Julian的支持,彷彿為他戴上強力的保護罩,對抗外間的惡勢力,好讓他從囚禁已久的身體一步一步走出來。
「『他』才是正確的代詞」
雖說Julian變得正面,但性別重置始終是個漫長又困難重重的過程,還需依賴同路人提供貼身的支援。Julian透過互聯網認識「跨性別資源中心」,也加入了女跨男的WhatsApp群組,與成員互相交換資訊,例如哪裡有藥物和心理輔導提供等。壓抑多年的他,決定從心理輔導尋找出口,然後從成員口中打聽到做性別評估的精神科麥醫生的診所。
一開始Julian向麥醫生坦誠自己性別模糊,麥醫生就照平常慣例問他幾條問題,分別涉及家庭、工作和人際關係等。 Julian回答後強調自己仍然處於性別模糊的階段,但麥醫生只是問了他一句:「你想用藥嗎?」他心裡想著能夠讓聲音變沉和臉型變得更男性化的願望,馬上就回答:「當然想。」麥醫生聽過他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後,告訴他:「你的確有性別認同障礙,是適當的時候開始用藥。」Julian感到驚訝的同時難掩喜悅,因為他萬萬想不到終於有人能夠認同他隱藏已久的內心世界,並傳遞配合和支持的訊息,令他可以積極地面對自己。
用藥後,有些朋友開始用「他」來稱呼自己,亦是Julian聲稱 「正確的代詞」,他覺得身邊一切的事情終於重投正軌。
「當你需要我們時 我們是存在的」
現在Julian經常關心自身以外的人和事,例如讓出自己做兼職的機會,主動伸出援手幫助其他跨性別人士找回自我,幫助他們變得更自主和獨立。他深信就是那種對自身性別的迷惘把大家聚集在一起,集結更多力量使得性別重置一事不再帶有那麼消極的情緒。
由於處於迷惘階段的跨性別者特別需要能夠提供支持的網絡,Julian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在一個名為「DISCORD」的平台上開設跨性別支援網絡,協助迷惘及母語不是廣東話的跨性別者透過網絡即時交流資訊。
Julian滿心歡喜地憶述:「只是短短數星期已有多達20人活躍於程式內,希望可繼續把程式發揚光大,亦歡迎香港人隨時加入,來個文化大交流, 從而幫助到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
「多元性教育刻不容緩」
Julian表示,現今香港的性教育確實不足夠,加上香港人思想比較保守,普遍忌諱談論性話題 。性話題不聊的情況之下,更多人不了解或者能接觸性別認同的話題。「當人面對不理解或沒接觸過的事情時,他們是無知的, 無知很多時候會造成恐懼,恐懼終會造成歧視,要打敗歧視的原點就要從教育開始。」
另外,Julian不認同要做手術才能轉變身份證上的性別,希望普羅大眾能夠明白,有些人的身體狀況較差,或不認為自己的身體需要開刀作出改變,不應執著要所有跨性別人士經歷一連串的手術,並帶來不必要的痛楚。他亦希望提倡性教育,這明明不是禁忌的話題,更應大膽拿出來討論,好讓更多人,尤其小朋友能及早了解社會的多元性別,從而學習用開放的態度討論性及性別議題。
他更希望父母能夠明白,性別認知不是子女任性的選擇,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才是讓子女勇敢面對自己的最大動力。
炸出一條彩虹 - Yin
文/Minnie Chiu

做自己,作出決定一直都是知易行難的事。為了做自己而走上跨性別之路,更難。「不是變性令我犧牲很多,而是變性令我脫胎換骨,將我糜爛的軀殼和心路歷程炸出一條彩虹。以前我只會看到灰色和黑色,現在我會看到光,看到顏色。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我會終於見到彩虹。」在Yin發光的雙眼中,我看到希望,他就是這個勇者。
「我可以挺起胸膛自信地過生活」
雖然身份證上寫著「女」,但Yin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是女生。在他對性別仍是懵懵懂懂的童年時代,只覺得自己和男生沒有分別,亦會和男生一起玩。直到青春期來臨,胸部開始發育,他才意識到自己生理上和一般男生有別。因為那令人煩厭的身體,他不願意照鏡子,也不喜歡自己的聲音,連聽到自己說話都會感到不舒服。他每天都會以腰封來束胸,將所有女性的特徵都隱藏起來,令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在外表看起來一致。這個策略似乎非常成功,身邊沒有一個人當他是女生。
直到他34歲時,Yin才知道香港政府醫院有提供性別重置手術,亦從那個時候開始,不斷去了解關於變性的資訊。不久之後,他便毅然決定找精神科醫生接受評估及協助。Yin在跨性別之旅的第一年,每月平均花2500元看私家精神科醫生和接受荷爾蒙治療,每三個月還要驗血一次,檢查身體對荷爾蒙治療的影響,了解會不會有排斥作用。經過一段時間的評估後,他獲得精神科醫生開出轉介信,並安排到醫院接受胸部切除手術。賀爾蒙治療讓他獲得更低沉的聲線,外科手術亦令他擁有更男性化的身形,終於可以挺起胸膛,自信地過生活。現在的他,每天都會留意自己身體微妙的變化,小心保護和愛錫自己得來不易的身體。
「我師父形容我是一個擁有雌性胴體的雄性」
Yin是一名廚師,工作環境中全是男性,但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當他是女生看待。他的師父形容他是一個擁有雌性胴體的雄性,除了身體外,他就是一個男性,和其他男性一樣生活,一樣工作。在他仍紮著胸部上班的時候,他的外籍老闆娘經常走過來叫他快點去做胸部切除手術,說:「反正你都不喜歡自己的胸部,為什麼要紮住它呢?快點去做變性手術!」
Yin雖然得到同事的鼓勵,但當他要作出這個決定時,仍十分忐忑,不知應該如何開口告知身邊的朋友。他想了想,決定先告訴一直鼓勵他做變性手術的外籍朋友,因為他覺得外國人比較開放,容易接受。於是,他就約了他的一班尼泊爾朋友到中式酒樓飲茶,告訴他們這個重大的消息。朋友們倒沒有太大反應,只問:「為什麼這麼晚才做?為什麼害怕說出來?」Yin認為,沒有反應就是最好的反應,原來身邊的朋友從來都沒有不接受他,更為他可以做回自己感到高興。現在,朋友會陪他健身,教他如何鍛煉肌肉線條。雖然跨性別之路仍很漫長,幸好他有一群好朋友、好同事,陪伴他繼續成為更好的自己。
「我很反對政府要求我們做重建手術」
Yin期待不久的將來,可以進行女性生殖器官的切除手術。然而,對於男性生殖器官的重建,他認為沒有必要。Yin說重建陰莖需要將尿道增長,香港的醫療技術仍未成熟,失敗的個案經常發生,尿道感染的風險亦很高。陰莖重建需要將前臂或小腿側面的肌肉組織、與直徑約1.5公分的骨骼、血管等整形後,移植到患者陰莖部位。而該陰莖基本上沒有多大作用,既不能自主性勃起,如廁亦有可能漏尿。況且這個手術並不是一次便能夠完成,有機會需要住院半年。他聽聞過某跨仔進出醫院進行了多達十二次的手術,也未能順暢如廁。他很認真地說:「為什麼本來健健康康,不會被人看到的性徵, 因為要做一個不必要的重建手術,而變得溶溶爛爛?」
Yin認為只需經過兩年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評估,接受過荷爾蒙治療,經歷兩年的真實生活體驗後,就足夠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做手術重建或切除不喜歡的性徵乃個人意願。Yin說他是女變男的跨性別人士,外表已經很pass(指不容易被看穿),社會對他的接受程度會高一點。然而,社會對男變女的跨性別人士接受程度比較低,即使她們的外表已經很女性化,甚至已經進行了性器官切除手術,但若身份證未改,進入女廁一旦被發現,仍會被指變態。所以,尤其對於男變女的跨性別人士,身份證上的性別,比她們的性命更重要。「跨性別人士已經很辛苦地做回自己,為什麼仍要強迫他們做不必要的重建手術呢?」
製作單位:跨性別資源中心
主编:梁詠恩、黃結梅
顧問:張佩琦
文字編輯:Lanlan Yu
作者:Lanlan Yu、Natalie Yim、Minnie Chiu、Carmen Wong、Eunice Chau
校對:Lanlan Yu、許二毛
本活動計劃由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
本刊物內容只代表本機構的意見
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場






